科技金融:中国经济跃迁助推器
发布日期:2025-07-15 作者:中阅图书 浏览量:333 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竞争趋于白热化。与此同时,各国长期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技术进步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最重要的因素。为此,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科技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提出,其既承载着支持我国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期冀,也是我国经济“火箭”能够跃迁进入高质量轨道的“第一级推进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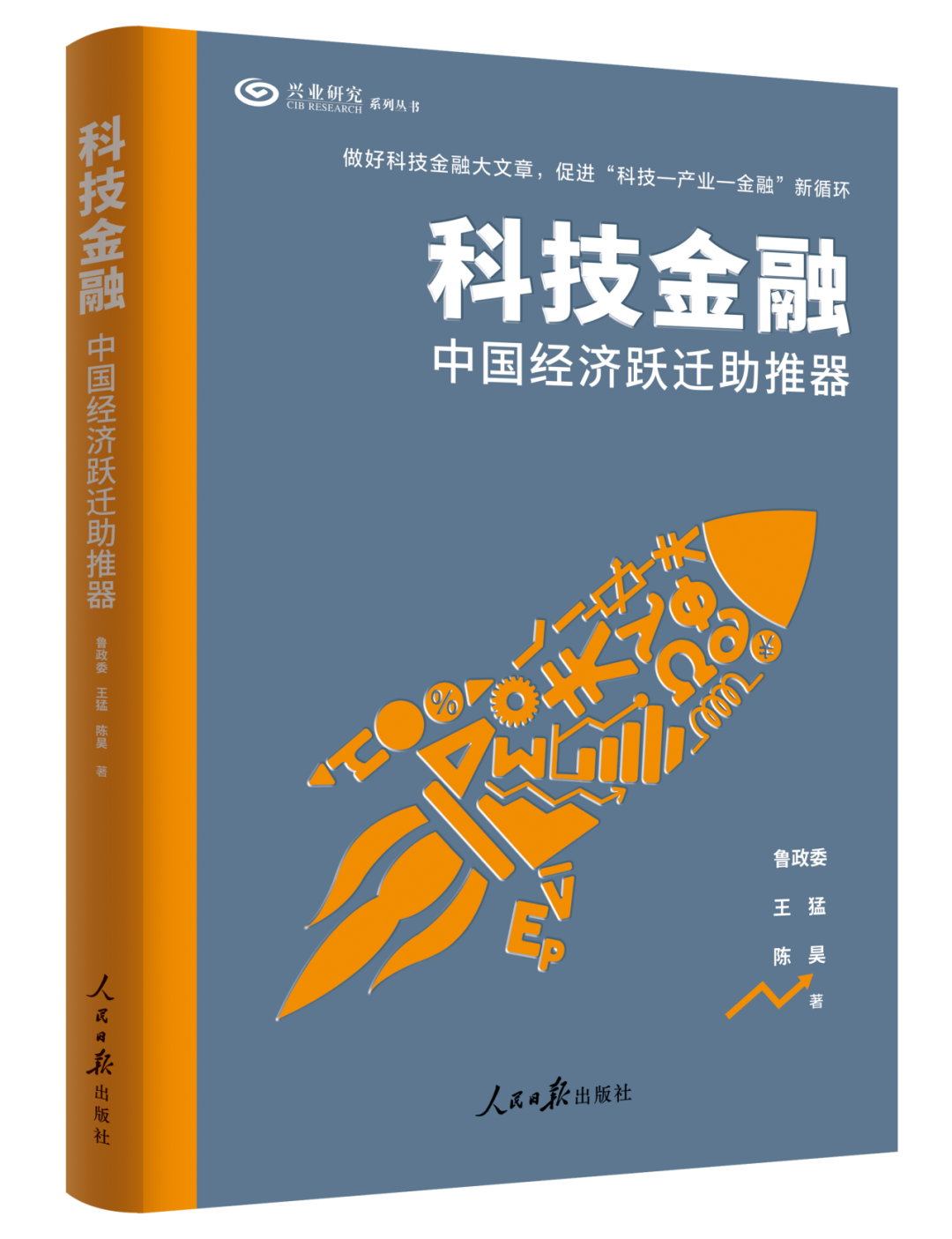
科技金融是金融,但要做好科技金融,却不能局限于金融,而是需要对科技演进方向、创新逻辑、产业规律等进行细致入微的理解。基于“大投行、大资管、大财富”领域的禀赋与优势,兴业银行早在2017年就确立了“商行+投行”的发展战略。有别于其他领域金融服务,支持科技金融发展不仅需要传统商行服务,更需要各类投行服务的有效支持,这也使得兴业银行自然而然成为我国科技金融的探路者。兴业研究是兴业银行致力于研究赋能业务的单元,我们的研究一开始就深深嵌入科技金融的业务之中。本书其实是我们在业研赋能过程中的体会和感悟,期待能够给我国的科技金融贡献一份力量。根据我们的研究,科技金融除金融外,还与产业、创新、政策等领域密切相关。
在金融与产业视角下,科技金融的重心应该与产业升级的方向相一致。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产业呈现从“引进成熟产业”到“培育新兴产业”、从“雁阵被动迁移”到“头雁主动出海”、从“低端环节转出”到“高端环节发展”三个趋势,科技金融应该契合产业结构演化。更进一步,金融不应仅被动顺应产业发展,还应主动推动变革发生。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希克斯提到,工业革命的技术早已存在,而之所以工业革命未能早早发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匹配的金融服务支持,以至于“工业革命等候金融创新”。陈雨露曾指出,以现代商业银行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革命为第一次工业大革命提供了大规模的资金支持,以现代投资银行为特征的第二次金融革命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重构了资本基石,以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第三次金融革命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缔造了新的推动力量。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赋予了金融业新的历史使命。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金融体系能否完成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使命,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既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我国从金融大国稳步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
在金融与创新视角下,科技创新包括六个环节。各环节的金融需求存在显著差异,需要精准匹配合适的金融供给,即针对不同的“锁”配不同的“钥匙”。具体来看,科技创新包括科学研究、概念验证、产品熟化、行业引入、行业成长、行业成熟六个环节。前三个环节(科学研究、概念验证、产品熟化)属于“创新产生”,以构建新理论为起点,以开发新产品为终点,具有投入周期长、产出不确定和产出外部化的特点,需要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三方接力。后三个环节(行业引入、行业成长、行业成熟)属于“创新扩散”,以出现新产业为起点,以产业成熟为终点,具有验证周期短、风险可估计、收益内部化的特点,适合包括商业银行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在内的商业性金融。
在金融与政策视角下,传统观点认为,创新就是纯粹的市场行为,把一切交给市场就好了。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成功实践表明,现实并非如此。以目前全球创新最活跃的硅谷地区为例,美国研究者阿伦·拉奥、皮埃罗·斯加鲁菲在《硅谷百年史:创业时代》一书中明确指出:“对于硅谷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应把功劳归于最大的风险投资者:政府。湾区的高科技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受益于技术军转民的最佳示范,也是政府进行整体干预的完美案例。”他们还指出:“风险投资发端于政府行为。1958年通过的《小企业投资法案》被认为是受到专业管理的风险投资行业的开端。”弗朗西斯·福山也指出:“硅谷在很多方面是政府产业政策(DARPA)的产物。”因此,政府的制度设计、财政资金(包括财政拨款和政府采购等)、政策性金融等,也是科技金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科技金融,不止是商业银行和私募股权,“需要一场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种子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商业银行融资、资本市场无缝对接的接力”。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对金融与产业、创新、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第二章研究了以美国为主的境外创新制度和科技金融模式。制度创新学派认为,技术创新需要设定有效的激励制度,以激励企业家精神;国家创新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需要激发企业家精神,还需要由国家创新系统推进。融合两种学派的见解,科技创新的制度设计既需要在市场有效的领域对创新主体进行激励,又需要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对缺失要素进行补足。具体来看,“创新产生”阶段市场失灵,其中,科学研究环节得到了财政资金的保障,但概念验证环节和产品熟化环节却容易被政府忽视。美国通过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和国家种子基金制度,较好地填补了这两个环节的资金缺口。“创新扩散”阶段市场有效,但不同国家在不同环节的成效有所不同。美国发达的直接融资体系能够有效促进行业引入环节的发展,但产业政策的缺失和摇摆使得美国对行业成长和行业成熟环节支撑较为乏力。之所以借鉴美国的创新制度和科技金融模式,是因为其在“创新产生”阶段构建了全球最成熟的创新生态系统,并造就了硅谷这一典型代表。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在“行业扩散”阶段有其独特的制度设计(例如德国的学会制度、日本的独立行政法人研究机构制度),而在“行业产生”阶段的中小企业促进政策、产业转化政策同样借鉴自美国,但未达到美国的实践效果。
第三章考察了我国科技金融的具体产品模式。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拥有最为庞大的总资产,也为各经济部门提供了最多的融资。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银行集团不仅拓展了传统贷款融资的模式,也逐步拥有了多种非银金融牌照,可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务。时至今日,商业银行已可以在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并购贷款、创新贷款利率定价机制、认股选择权贷款、跨区域联合授信、基金债、表内股权投资和特殊目标收购公司等领域为科技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其中,“认股选择权”是商业银行服务“早小硬”企业(即科技小微)的关键工具。科技小微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在一般信贷模式下面临着“两头不靠”的融资困境:若简单按普惠小微的模式来融资,由于单笔额度偏低,导致“不解渴”;若简单按照科创贷款的模式来融资,由于尚未获得科创称号,导致“够不着”。附加认股选择权的贷款作为一种创新模式,通过分享科技小微的潜在高收益,来弥补银行潜在的高风险,使银行有能力成为服务“早小硬”企业的“耐心债务资本”。
第四章探讨了我国科技金融客户界定、兴业研究科技行业分类和科技行业分析框架。科技金融客户的界定口径包括科技型企业口径和科技相关产业口径两类:前者是对“企业”进行界定,具备特定标签的企业均可看作科技型企业;后者是对企业所在的“行业”进行界定,选定行业下的企业均可以归入科技金融客户。然而,在科技相关行业口径下,由于细分行业颗粒度不够精细,导致统计数据过于泛化,同时科技行业内部尚未建立统一的标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兴业研究尝试编制了《兴业研究科技行业分类》。随着科技金融的授信模式逐渐从“数砖头”的抵押模式转向“看发展”的信用模式,对银行机构科技行业认知能力的要求不断提升:银行需要看懂前沿技术,解读商业模式,预测发展趋势,明确企业在行业中的位置,评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未来的偿债能力。鉴于业务人员需要花很大精力才能看懂不同的行业,因此需要构建一个基于产业竞争视角的通用行业分析框架,从而使其快速把握行业发展趋势。该通用框架由两个共性指标构成:一是渗透率,体现产业生命周期和需求总量;二是国产化率,体现国产替代进程和供给结构。为了弥补单一指标的局限性,我们建立了“渗透率—国产化率”的二维分析矩阵,并将行业对应至具体阶段。
第五章细化了科技金融在操作层面的业务方法,旨在解决“企业好不好”和“好企业能贷多少”的问题。科技企业的特点是硬信息(定量的、客观的信息)少、软信息(定性的、主观的信息)多。由于软信息更难采集、传递和使用,加剧了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造成银行内部业务流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在审贷分离、风险控制逐层收敛的业务流程中,软信息在银行内部传递过程中严重流失,最终会导致银行决策趋于保守。解决这一堵点的关键在于软信息的使用。在企业评价方面,我们期望通过考察技术创新、行业趋势、公司治理和资金流转这四类软信息,对科技企业进行综合评价,进而助力业务人员把握现状、预测未来,回答“企业好不好”的问题。在审查审批方面,结合《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及技术流理念,我们建立了科技企业授信测算方法,实现了软硬信息结合的授信额度测算,从而回答“好企业能贷多少”的问题。

